在笔者看来,游戏主要有两大关键部分:一是学习和互动,玩家要在游戏里发现各种潜在规律,搞清楚不同元素如何搭配运作,学会操控它们并提升自己的能力。二是融合多种媒体形式,比如文字、音效、音乐、剧情故事、美术画面和动画片段等。这些元素就像给游戏的核心机制 “穿” 上了具体的 “外衣”,让玩家更容易理解和代入,从而构建出一个让人沉浸其中的虚拟世界。
从整体来看,游戏最大的魅力在于能让我们暂时抛开现实中的烦恼,“跳出” 真实的自我,进入一个充满想象的虚幻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:我们能实现现实中做不到的事,体验新鲜事物、“游览” 新场景,甚至 “成为” 另一个角色;我们能掌控游戏里的环境,付出的努力会有明确的反馈和奖励,而且完全不用承担真实的风险;离开游戏时,我们往往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得到了提升,自我感觉更好。
因为游戏能带来这种多方面的丰富体验,才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它,在大众市场里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。
但是如何去做好上诉的一些内容,其实是需要分很多层面去思考的。
游戏设计者的角色
我们作为游戏设计者的角色最终是创造一个迎合目标受众需求、欲望和能力的产品。这意味着支持、教导、培养和激励玩家。创造一种氛围,让玩家感到舒适和控制,因为他们相信你不会用他们还没有机会准备的事情来挑战他们。你的角色是关心玩家的需求——给他们令人兴奋的新东西看,让他们学习,让他们掌握技能,让他们克服挑战。不要用他们以前见过的刻板印象来烦他们——用新的概念、新的想法和新的经历来刷新他们。
那么,如果游戏提供了大量娱乐玩家的机会,我们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让玩家从游戏中获得快乐呢?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游戏更有趣?之前看到过一句话:
“它只是你投入的一半;另一半是人们从中得到的东西”。
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,我们往往会不知何故地陷入这样的境地:我们不得不为我们不太了解的人买一份礼物。挺难的!我们通常最终会送他们一些像鲜花、巧克力之类的东西,我们知道大多数人至少不会不喜欢这些东西。如果他们这样做了,他们可以把它给别人,如果他们自己也有同样的情况。作为一名游戏策划,如果你试图为一个你不太了解的人设计一款游戏,你也处于类似的境地。这就是我们做市场分析和用户调研的原因。
用户画像
相信用户调研是我们做游戏经常做的,核心思路就一句话:别拍脑袋瞎猜陌生人喜欢什么,用数据精准锁定目标人群!

收集数据:找目标用户聊天,问问他们的年龄、性别、平时玩游戏的习惯(比如每天玩多久、喜欢什么类型),还有兴趣爱好(比如爱看什么电影、听什么音乐)。这些信息能帮你画出用户的 “基础画像”。
分组归类:把收集到的数据整理到 “用户网格” 里,就像给人分类贴标签。你会发现有些人虽然看起来不一样,但年龄、兴趣、游戏习惯很相似,这些人就可以归为一类群体。
打造典型人设:给每个群体编一个 “虚拟代表”,比如 “27岁的中产男性Bob”,他可能喜欢策略类游戏、爱看科幻电影、追求游戏画面质感。这个“Bob” 不是真实存在的人,但能代表这一类用户的核心需求和行为特点,帮你更直观地理解他们。
测试优化:游戏开发得差不多时,找真实用户来试玩,看看他们对游戏的反馈。比如 “Bob们” 觉得某个关卡太难,或者喜欢某个角色设计,就根据这些意见调整优化。
调研时别只看表面,要深挖用户兴趣、技能、品味背后的原因。比如有人喜欢古风游戏,可能是因为从小喜欢历史,这时候你在游戏里多加点历史彩蛋,就能戳中他的需求。如果直接问用户 “你想要什么游戏”,那肯定是很傻的,大多数人说不清楚,除非你拿出具体方案让他选。但如果遇到懂游戏设计的玩家,一定要认真听他们的想法,说不定能挖到宝藏创意。很人不愿意听用户意见,结果错过很多好点子。
记住:用户的真实反馈永远是优化游戏的 “金手指”。
游戏宽度
我所说的“游戏宽度”基本上是指游戏触及了多少不同的需求和欲望。如果我们迎合各种各样的需求和愿望,我们就有可能接触到更广泛的受众。如《模拟人生》系列,允许玩家自主选择目标。
但迎合许多需求和欲望并不一定意味着满足需求和欲望——我们比这要具体得多。我们必须考虑目标受众的具体兴趣,以及他们可能涉及的内容。如果游戏的设定或风格不吸引他们,或者他们不理解,那么他们很容易流失,不管它有什么其他品质。
创建一个宽的游戏在很多方面都是好的,但是我们想在游戏中包含的东西越多,制作起来就越困难和昂贵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管理这一点,那么它可能会对游戏的质量产生负面影响,进而可能导致玩家的“流动”减少。归根结底,我们想要(或能够)投资多少钱,我们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,以及我们希望从投资中获得多大的回报。更广的游戏可能会赚更多的钱,但它们的风险也更大,制作成本也更高。
模仿
模仿是我们天生的学习方式,而且贯穿我们的成长过程,在游戏里更是体现得明明白白:
1)小时候:模仿是认识世界的方式
边玩边学:小孩子会模仿大人说话、扫地、过家家,把现实里看到的人、物体、规则都 “搬” 进游戏里。比如玩 “医生看病”,其实是在练习怎么沟通和使用工具。以前我自己就喜欢用泥土和弟弟妹妹一起搞过家家。
偶像崇拜的底层逻辑:小孩喜欢模仿超级英雄、公主、电影角色,因为这些人是社会默认的 “榜样”。通过扮演他们,孩子能理解什么是 “好”“坏”,也会想象自己长大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比如《哈利・波特》火,就是因为很多孩子觉得自己和哈利一样 “特别”,能产生共鸣。以前《火影忍者》上映在国内的时候,我也经常试图去尝试他们那种忍者结印,也会对于佐助这种人设感觉很棒,喜欢模仿他的样子。
2)长大后:模仿是 “换个身份爽一爽”
长大之后的模仿可能和孩提时代不太一样。很多成年人模仿游戏角色,更多是觉得 “好玩”,但不知不觉也会 “代入感上头”。比如你玩《赛博朋克》里的黑客,操作久了会感觉自己真的掌握了酷炫技能,大脑甚至会给你 “虚拟成就奖励”,暂时忘记现实里的压力。
玩游戏=选 “临时人生”。我有个朋友玩《模拟人生》时,为了让虚拟角色不丢工作熬夜哄他睡觉,结果自己凌晨3点还没睡 —— 这就是典型的 “角色需求盖过真实需求”。但反过来想,这说明游戏成功让他 “入戏” 了。

而对于游戏而言,玩家选的不是游戏,是 “想成为的自己”。角色设计是核心吸引力,玩家挑游戏时,本质是在挑 “临时身份”。比如有人想当末日幸存者,有人想当商界大佬。
如果目标用户喜欢的角色差异大,不如设计多个可选角色,甚至开放 “自定义捏人” 功能。比如在手游《原神》中,玩家既能选择精通元素力的 “草系学者” 提纳里,在雨林中研究植物与生态;也能成为掌握冰元素的 “社奉行大小姐” 神里绫华;还能通过 “尘歌壶” 系统自定义虚拟形象,搭配不同服饰与动作,甚至打造专属角色背景故事 —— 从高冷剑客到活泼吟游诗人(温迪),多元角色设定几乎覆盖了 “二次元” 受众对 “理想自我” 的想象空间。

游戏其实就像一面 “虚拟镜子”,玩家通过模仿角色来探索 “理想中的自己”。设计者要是能摸透玩家想成为谁,就能把游戏做成他们的 “第二人生实验场”—— 毕竟,谁不想在虚拟世界里过把 “不一样的瘾” 呢?
未经授权请勿用于任何商业用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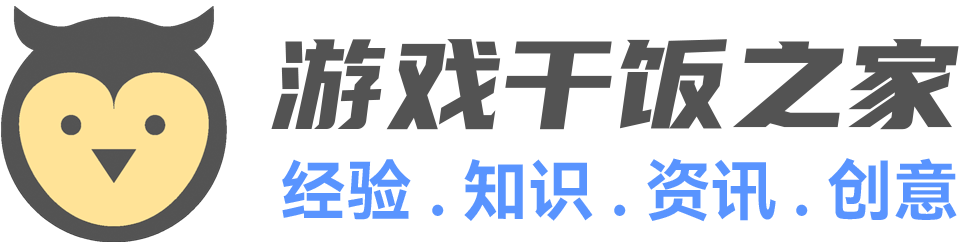




发表评论